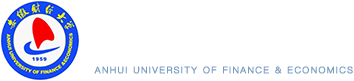1985年,夏
屋前小路两边有一片茂密的竹林,夏季叶盛时身处其中往往不见天日。持续不断的虫鸣声冲抵着林间的那一抹阴寂感。那是一种生在竹上的独角虫发出的,听说胆大的孩子抓到后会烤来吃。弟弟们寻觅着虫子,而我独自一人蹲在一旁,满怀期待地望着远方林荫尽头。
“我回来咯!”
远处传来了父亲的声音,我敢肯定,如果有锣鼓的话他一定会边敲边喊的。
带着弟弟们跑了过去,看到还远在田间的两个人影和一辆牛车。车上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电视机。还有一个比电视更高大的黑色箱子,听他们说那玩意儿叫音响。
自从乡里砸了公社的“大锅”以后,父亲便开始发动乡里的人们养牛,把牛犊交给他们,养大后再花钱收回。后来许多人家地也种得少了,荒了的田地正好用来养牛。自家里也不需种很多菜,记得很多人家会时常送来。
父亲经常出门,每次回来都会带些稀奇物件回来。
家里成了村里少数有电视音响的人家,通过电视,我也成了村里少数对外界充满向往的孩子。
2001年,冬
我只记得爷爷躺在藤椅上一动不动,似是睡着了,我拿着蒲扇不知道是给自己扇还是给爷爷扇。那是我对爷爷的唯一印象。
我和奶奶两人住在一个硕大的院子里,院子里常年摆着一个鼓风机,我一直以为那是匹木做的牛,总是试图爬上去而被奶奶阻止。每年割完水稻后,我便学着大人的样子去转动把手,但太矮了总是转不了一个满圈。奶奶笑着说我帮倒忙,我便更努力地转着。
庭外有一片竹林,生了竹蜂,我觉得他们的头上的角很适合打架,便经常跑去林子里抓几只让他们斗上一斗。
有一天,有两个穿着很奇怪的人从林间走来,让我叫他们爸爸妈妈。我跑回去找到奶奶,拼命抱住奶奶,生怕被坏人抓了去。奶奶说:“叫爸爸妈妈。”我不肯叫,他们拿出了一盒水彩笔,我接过来把玩起来,却未消除对他们的恐惧,仍不敢太靠近他们。
过了几天晚上,吃完饭我在藤椅上睡着了,朦胧中感觉到那个男人把我抱到了床上。半夜醒来后发现睡在旁边的不是奶奶,哭闹起来,想让隔壁的奶奶来拯救我。结果哭累了还是就这样睡着了。
爸妈临走时,带我去了幼儿园见了将来的老师,给了她一袋全是红色的水彩笔。老师兴奋的表情令我感到意外,因为我收到的可是全彩的。后来我常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看到红色水彩笔的印记。
1993年,秋
屋外的竹林经秋风一吹,终变得稀疏。路两边堆积的枯叶也越发的厚。没有了虫鸣声,竹林变得阴沉沉的。我依旧时常望着路口。
走之前父亲异常兴奋地说:“这次是个大机缘,事成了我们举家搬去首都北京!”
傍晚,许多人家开始生火。随着几声不起眼的犬吠,父亲终于回来了。
跪在父亲的灵棚里,我想:北京真的有那么好吗?
2010年,夏
从小学一直读书到现在已经是初中了,暑假实在百无聊赖便独自一人回了老家。
循着记忆中的方向,一路披荆斩棘找到了那座老旧的土房。硕大的院子里长满了比人还高上一撮的野草,门上还依稀能看到贴了门神的纸,门栓上吊着一把满锈的锁,墙上爬满了龟裂的纹路,好似说话声音稍大一些都足以让这座房子坍塌。
茂密的竹林又引来了夏虫的青睐,然而单调的鸣叫声再也不能让这里生机勃勃了,即使正当夏季,原本的路上也被层层枯叶吞噬。当年那些抓虫儿的小孩,都去往了没有竹林的地方。
听父亲说当年爷爷打算做一桩买卖金条的生意,结果被人骗了。身体染恙,就在这间房子里辞世。
回到奶奶现在的居所,庭前是一片开阔的水稻田,翠色已开始慢慢褪去。奶奶说到时候收割机会来,我望着田间的泥泞小路,很是怀疑它如何能开得进来。
1995年,秋
“我们家的红薯又被人挖啦,铁定是王二家干的。”
父亲走后,家里只能靠妈妈一人种田养活。每家每户都有好多张嘴,大都吃不饱。王二家仗着我们家中无成年男丁,经常欺负我们。
那时我正高二暑假回家。
我挑了跟粗柴棍,向田间跑去。正好看到年纪与我相仿的王二家三儿子蹲在他们家田地旁,老三见势不对要跑,却因为没有穿鞋几次打滑,终于被我追上。
我冲上去二话没说往他肩上来了一棍。他没反应过来,第二棍我敲到了他的背上。
老三很痛苦地趴在地上,艰难地喘着粗气。我不敢再打了。
“以后不准再动我们家东西!再这样下次换刀跟你们拼命!”
说完扛着棍子扬长而去。
几天后,王二家老大老二逮到了正在田里干活的我,两人先是一番理论,说凭什么打我们家老三,现在还在家里躺着。见我不说话,几拳下来,见了血。
好在几个弟弟早早地去叫了人,乡里人们拆开了仍在泄愤的他们。
我转身拿起了锄头做势要锄人。所有人都吓到了,连忙一边劝阻我一边数落王二家两人。王二家两人见状,也没了底气,落荒而逃。
后来王二家仍总是喜欢占着我们家些小便宜,但总算不敢太过分。
第二年,我坐火车去成都读书。
学费在车上被人扒了去,无奈去少林寺学了一年功夫回家。
从此家里再也没有能力供养出一个大学生。
2016年,春
“你奶奶身体越来越差了,得想办法把她叫出来住”
“去你们那吗?”
“都行,只要有人照顾就好”
我大学从广东考回了四川,虽说有了机会可以去看看奶奶,一年也难得见几次面。
除了我们家在惠州,几个叔父各自在成都和杭州定居。听说当年受三峡移民影响,父亲一家人都不想听从安排去新疆,各自讨要车费选择了不同的地方打拼。只留下了奶奶一个人在老家。
父亲在广东安定下来后先把我接出去读书,后来接奶奶出去。但没多久奶奶就说住不惯又回去了。
我决定回老家把奶奶接到成都住。
听说家里的马路修好了,按以前的泥泞路,两个小时的火车,两小时的大巴,半小时的徒步路程,如今应当一半时间足矣,我盘算着。
然而混凝土铸成的马路上全是压烂的坑洞,因此整个行程也并没有快多少。
门前原来我们家的稻田被马路占用,两旁零散的田都生起了一种形似芦苇的杂草。只有连成一片的大一些的田地才见有着整齐的农作物。这些作物,养活乡里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人还有富足。
我跟奶奶说想再去老房子看看,奶奶说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,以前老房子竹林边还有棵花椒树,自己有时还去摘一些,现在已经老了被虫蛀了,就再也没去过那边。
带奶奶走的时候,望到蜿蜒远去隐于山林的马路。马路两旁有许多破旧得随时要坍塌的房子,却被人刷上了一层白白的粉。“今年的危房改造项目”,奶奶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