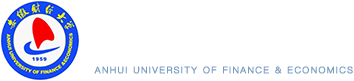我习惯了她等我。
她第一次等我,是在 1939 年,当时中日战争日益激烈,国民党组织计划在舞蹈课上暗杀日军高官元鹤本武。她是那堂课的舞蹈老师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开始慌了,将她带回家给她订了船票让她赶紧走。她问我,我能不能和她一起走。我说,一个人习惯了。
那天晚上我和她跳了一支舞,舞蹈结束时我揽着她的腰肢定定的注视着她,她洁白的颈舒展的后仰,像一只美丽的天鹅。她的眼角有泪划过。她问,我能不能等抗战结束来找你。
她第二次等我,是在1945年。我因刺杀元鹤本武入狱六年,终被释放出狱。我在舞蹈教室里见到了她,她先是拘谨的笑了,然后越笑越释然,越笑越大声,然后飞扑过来紧紧抱住了我。我开始给她装修教室,用最好的料子请最好的工匠。我跟她说,我们生个孩子吧。她笑的满脸喜悦,好。接着国党给了我极高的提拔,组织要我迎娶前副参谋长的遗孀来巩固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。我和她说了,她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她满含哭腔的说,我们的房子才刚装修完,然后又挤出笑意过来问我,你能不能不去啊?我强硬着说,不能。她跌坐在楼梯的拐角,双肩激烈的耸动,吊着一口气断断续续的说,等抗战结束我一定来找你。婚礼那天,觥筹交错。在一众哄笑贺喜里,我笑的热泪盈眶。
她第三次等我,是在 1949 年,国党政权全面崩溃,核心人物转移去了台湾。我回到了重庆,跟着组织行进。在十字路口,我遇见了她,她对着我笑得开心。我将她带回根据地,帮她褪下脚上被血粘着的袜子。她一边疼的抽气,一边笑嘻嘻的和我说,我每到一个地方仗都刚刚打完,嘶,这是最后一个地方,最后一场仗。你看啊,仗总有打完的一天啊。我抱了抱她,说,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那天夜里组织突然下达重要指示,和我说,南京解放以后, 主席就把攻打台湾的计划摆到了日程上。让我在继续坚持半年。我携着她在雪夜里漫步,抱着她在她耳边哼出了我们跳过的第一支舞曲,她像一个雪中的精灵,美丽得不可方物。我和她说了组织的计划,那一刻她几近崩溃。“你不是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吗。” 我说,你回去吧。那天我独自一人奔赴战场,身后满是炸开的火光。
1987 年我终于回到了家乡,组织告诉我她在我走的那天挣脱了带她离开的人,飞蛾一般死在了我身后的火光里。 我感到了一丝怅然。 后来有个文笔极细腻的叫做黄碧云的女作家在她的《无爱纪》 里这样写道“在这难以安身的年代,岂敢奢言爱。”
我习惯了孤军奋战。 我习惯了先国后家。我习惯了她在身后等我。 我本以为她会一只等着我的。